惊异,目视,爱,许多灵思和故事。选自《马雁诗集》,挑出个人尤其喜欢的,乱序,比较随意。未完,或许会再增删。得空再把她的诗论也发些出来。诸君可以选出一些,再加评点讨论。
 (资料图)
(资料图)
“她才华横溢,尚在摸索,若再有十年,必修成正果——让我深感上苍的残酷:一手赋予她柔情与才华,一手又把她轻轻捏碎。”(北岛)
热的冷
献给soumir,和我的灵魂
我从来没想到,我的灵魂会是那样。
这灵魂,轻盈、孱弱,并且羞涩。
如同一面可能之镜。一个幻象的坍塌
牵动了世界的粉碎。那短暂的一瞬,
灵魂睁大眼睛,穿过空气中的尘土。
好象玻璃器皿中的热水,干玫瑰的红
渗开……稀薄的,游离于空无,
寻找那命中的命,血中的血。
2002年夏
情诗
熟悉决然割破了我。
我的心并非绝无情分,
此刻它正渐渐离开。
空气并未变得更稀薄,
的确,水是清澈的。
你的呼吸如此紧凑,
热烈而且清洁。
我告诉你我看见了海,
“海……是大的”。
你走,穿过人群,
对陌生者举起双手。
那一对掌心是清白的,
我很清楚这种爱。
2003年夏
傍晚,看一场雨……
如同一把花伞。从四十米的空中,我看到
幸福。那些幸福,那些琐碎、远离优美的东西。
它们安静地穿过潮湿,在不确定的绿表面,滑翔。
我怀疑它们就要接近我,我怀疑幸福正在颤抖!
然而,那些经得起敲打的,在迅猛的力对面的,
安静着,不再张望的,正在穿透的,不是雨水;
我抬头看到的,正在坠落的,我断定:不是液体。
它们飞快地坠落,丝毫不把自己看作天使,丝毫
没有我的犹豫。我怎么可能不怀疑,怎么可能
看着注定与我隔膜的人流,在我身下涌动,还保留
一颗冷冰的心脏,或者两只对称的肾!我期待
来只猛禽,把日日滋生的内脏拿走。这些毒素,
这些物质的幸福。它们就要飞起来、融化,
就要汇入陌生的水。成为所有陌生的事物。
2001年夏
冬天的信
——给马骅
那盏灯入夜就没有熄过。半夜里
父亲隔墙问我,怎么还不睡?
我哽咽着:“睡不着”。有时候,
我看见他坐在屋子中间,眼泪
顺着鼻子边滚下来。前天,
他尚记得理了发。我们的生活
总会好一点吧,胡萝卜已经上市。
她瞪着眼睛喘息,也不再生气,
你给我写信正是她去世的前一天。
这一阵我上班勤快了些,考评
好一些了,也许能加点工资,
等你来的时候,我带你去河边。
夏天晚上,我常一人在那里
走路,夜色里也并不能想起你。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这让人安详,有力气对着虚空
伸开手臂。你、我之间隔着
空漠漫长的冬天。我不在时,
你就劈柴、浇菜地,整理
一个月前的日记。你不在时,
我一遍一遍读纪德,指尖冰凉,
对着蒙了灰尘的书桌发呆。
那些陡峭的山在寒冷干燥的空气里
也像我们这样,平静而不痛苦吗?
2003年冬
公共汽车纪事
闷热,更热的是车厢后部
起伏的浪,我如此谨慎。
之前,抑郁症患者的前身
从南中国的裤兜里悄悄掏出
食指与拇指之间的钞票,避人眼目,
潜伏,正在接近伟大传统。
售票员收走湿润的钞票,两张。
在传统中,存在着“一”的可能性,
但有人说:“二”不能出现为“一”。
当时,它们依靠汗液黏着、紧贴。
喊号子的人此刻正经过窗外,
他们面无表情,并且不着一物。
热的振幅里,波荡的中心
正在人体内移动。没有
无谓的人物,这里正是拥挤的尽头。
身下,发动机还在创造新的人生,
此刻,抑郁症脚踏菲薄的地壳,
胸中涌起难以排遣的犹疑。
要用坚毅的嘴角抵抗源源不断的词语,
要穿过密不透风的人群。他们体内的热,
如同怀着炙烧的阴谋,迟钝地杵。
我粗暴起来,不再沉浸于想。
像冰,迅速穿透伟大传统的中心,
融化了。现在,同肮脏的土混合着。
2002年夏
星期天,我坐在玻璃上……
光照到地板上,反射,扎进一小片皮肤。
热也能是痛。敌人潜伏着接近我小小的领地,
带来他们的冷和甜。是那样甜,竟然也
能是咸与涩。那些在白炽灯下脱下外衣的人,
那些脱下内衣的人,不知道自己在动作的一瞬
扭动了。细小的腰,狭窄的臀。他们身体的
一小抹肉色,一小撮黑色,和红。扩大着,
倾斜进茫茫的白昼。这白昼里的旅行,滚烫地
穿过物质,穿过严密的逻辑。星期天,我
坐在玻璃上,坐在无边的翅膀上……回味
胆怯的话,菲薄的热情。不能融化的,仍旧
坚硬;阴影也没有可能抹去它的锋利。即使,
被一个个光斑晃花了眼,即使交叉的裂缝
拨动了脆弱的耳膜,这伟大的情种也不敢
掉头而去。不敢在这正午做夜间的啜泣。
2002年秋
七月的一次炎热晚餐
她们坐着,两两相对
互相瞪视对面女子的鼻梁
以及鼻梁两侧的眼睛
没有人说喝酒
晚餐的过程是平和的
一锅鱼汤以及四份凉菜
金属的筷子在她们指间滑动
因为汗液,
益发的光滑了
准确的说,她们是一群不合格的女人:
她们抽烟,夜不归宿
甚至在背地里搞同性恋
此刻她们是纯洁的
餐巾纸握在左手
右手礼节性的慵懒着
空中选准了角度悬着
然后探向一片萝卜
或者未知的另一种优美
她们开始走神
四条腿已经相撞,依靠着
剩下四条在犹豫
一些音乐传来,于是沉默
隔着桌子可以望到对面的
低胸装开口,和她的睫毛
她吹口哨
她说:看什么呢?
一碟菜没了,汤剩下了
她说,浪费
另一个人撇撇嘴
后来时间过去了
她们起身离开
很多条腿在众目睽睽下
领走了她们
2001年夏
采花贼的地图
第四个 白石桥(脸上有疤的乡下女人)
她来了,她走过来,震撼着一条笔直的大道。
要堵车了,肯定要堵车了,因为她来了。
大雨将至的消息传遍白石桥以北17个路口。
谁要拿着一只桔子到她家去叩门,
公布三年来音信全无的事实,谁要桔子?
她走路有风,她说话绝对没有停顿。
人人都在期待她的晕厥,倒地,和口唇边的白沫。
而她,乘坐公共汽车奔向远方,留下
一地桔子皮,留下辛辣的气息。
2003年春
我尊重你的复杂
我尊重你的复杂,一切
都合乎情理——再搞些个
愁苦的镜头,也无济于事。
好几年了,我趴在阳台沿上
偷看你摆弄人性,或捏造
一个银灰色飞行器模型。
出乎意料!我竟迅速长成,
直接进入中年的沉静与执着。
我迷恋你,数十年如一日:
复杂,如密密麻麻的格子
为了互相混淆,而面目相似。
每个毛孔里,藏一个魔鬼,
各不相同。每秒钟制造
一个新的欲望。冰冷僵硬
如水泥所造尸体,你是
完美无生命体。而我则是
简单,你看我如此简单,
作为你的反对。当我说出
“正确”就意味着结束。
此刻,万物凋零正是时候。
2004年春
细小的门
我曾经在三层楼高的地方
看见过,细小的门
它在操场的对面
一堵孤立的墙上,墙是灰白色
当时,我闻到肥皂的香气
回忆那道门的时候
我形容它,是寒冷的
对,是凛冽的肥皂的寒香
四年前,我又看到了它
在一个晚上,经过了短途的奔跑
我来到一间教室,在一个女孩子身上
我看到了它,细小的门
在她的身上有着针尖一样的芒刺
这门,似乎和恋爱无关
它是我个人的门
只出现在某一个瞬间
我正沉浸在酸楚中的时候
它出现了,它从来没有敞开过
现在那堵墙已经不在了
我甚至不能清楚地看见它
但很清楚,它一直在
这细小的门
2002年夏
痛苦不会摧毁痛苦的可能性……
痛苦不会摧毁痛苦的可能性,生命
不会消失自我的幻觉术。在一生的
时间里,穿越过岩石缝隙里的贝类
是潜藏的隐微的音乐,那是宏大的
乐队在奏响,人们正从缝隙里行军
去往伟大的未来。是的,光明将从
最卑微处散发,所有最恶劣的气味
是大战乱的征兆。我坐在垃圾堆上
唱歌,唱一支关于塑料和火结婚的
歌。这支歌将唱响至地底的孤独者
升起。他升起时,无花果树将开花,
贝壳将给出回环的路径,一切再次
降临,并反复以至于无穷。是这样;
他说:痛苦不会摧毁痛苦的可能性
2010-2-25
桥梓镇
它被剖开,像没长成的西瓜,
粉红色、无籽,人们这样定义孱弱,
就说:“桥梓”。一条浅灰色马路
小心地穿过它,尽量无痛,
人们在镇上来回,尽量无痛。
是啊,这可能存在的爱,
就像穿行的人群与道路之间
可能的默契。还能如何呢,
一次性对剖开的嫩西瓜,
无痛苦的生涯,正是人们的信念
在此处反复践踏。反复践踏,
想消失者无法消失。想存在者
拼命挣扎,反复抨击
自身,直至成为碎片化为粉末。
又反复成形,反复成为自身。
这是不灭的桥梓镇。人们
在小镇上来回走,成千上万的
脚印变成部首。然而,现实
质朴而具体,就像锋利的一刀。
准确。迅速。
2010-9-18
北中国
人们常常想起盛大的气象,
四季不断地变换着的痛苦,
是披裹在北中国的大披风,
他从来不变换自己的外貌,
然而谁知道这是不是一个
幻象?河南人假装爱撒谎,
河北人假装爱吃鸭梨,和
山东人、山西人一起研究
各种通今贯古的重大问题,
其实也只是一组经典剧情。
北中国,是这样一个简单
准确的命名,幸福宏大得
如同天干地支,不可摧毁。
还有什么呢,人们希望着
有什么样的责任降临,有
什么样的大运动再次发起,
其实不,我们只要简单的
市俗生活,卖大葱的货车
停泊在路边,扩音器单调
而热诚,土豆在地上打滚。
2010-9-18
在小山上看湖
晚上八点,
我们四人在小山顶的露台上看湖。
她俩在我右侧,他在我后方,
松松散散地站着,互相呼应。半侧身子。
椅子在身后不远处。靠着栏杆,
一口一口抿菊花茶依稀的甜味。
稀疏的树冠围拢,湖面只一亩大小,
远一点是路灯。更远的公路上有汽车。
她说:“空气真好,感觉真好。”
我说:“是的,连工地打桩的声音
都显得不难听了。”
我们像情人一样沉默,
像看情人一样看湖。
2010-10-5
我们乘坐过山车飞向未来
我们乘坐过山车飞向未来,
他和我的手里各捏着一张票,
那是飞向未来的小舢板,
起伏的波浪是我无畏的想象力。
乘坐我的想象力,他们尽情蹂躏
这些无辜的女孩和男孩,
这些无辜的小狗和小猫。
在波浪之下,在波浪的下面
一直匍匐着衰弱的故事人,
他曾经是最伟大的创造者,
匍匐在最下面的飞得最高,
全是痛苦,全部都是痛苦。
那些与我耳语者,个个聪明无比,
他们说智慧来自痛苦,他们说:
来,给你智慧之路。
哦,每一个坐过山车的人
都是过山车建造厂的工人,
每一双手都充满智慧,是痛苦的
工艺匠。他们也制造不同的心灵,
这些心灵里孕育着奖励,
那些渴望奖励的人,那些最智慧的人,
他们总在沉默,不停地被从过山车上
推下去,在空中飘荡,在飘荡中,
我们接吻,就像那些恋人,
那些被压缩在词典册页中的爱情故事,
还有家庭,人间的互相拯救。
如果存在一个空间,漂浮着
无数列过山车,痛苦的过山车……
2010-12-2
我们最后走到同一个地方
为韦源
你,修建水泥森林的人,即使
拿起颜料笔,也不能画伟大的画。
你不可能得到你想要的,你不可能
生吃掉耀眼的阳光,你吃日光灯。
你吃机油,你吃冰凉的石头,
但你不能吃掉一个字,不能
指望一个符号卡在你的牙缝里,
并且发芽,长出一张象牙似的脸。
我是污水里升起的神,我只要
一抬腿就得到一切。只要,张开
泥浆中的眼睑,我就照亮钢铁。
这钢铁就是黄金。我举起胳膊,
就飞到空中。我命令你歌唱。
你暗淡的眉毛就必须被点燃。
这火有比一亿吨钢铁融化还要
多的热。你尚未建成的森林
破土而出。这些病毒,这些恐怖。
它们啃掉你的睡眠,给你痛。
把痛给我!我,就是这滚烫的
水中的神。我们是从水中发生。
最后,以水的名,我们相认。
2003年春
灌水
我拿着我的杯子
是我的杯子
我确定无疑
我拿着它抚摩它
是我的杯子
塑料杯子
不容易摔碎
还不烫手
温度被隔绝
在另一个空间里
我又拿了四颗酸梅
不多不少
顺手就拿了四颗
美好的数字
简单的定义了美好
我进一步开始我的灌水行动
在路上
我遇见了上司
他说:哈哈,胖大海
我说:不,不是的
真的不是的
我要否定他们
否定所有错误的关于灌水的定义
我低着头说
不,不是的
所有的,都可以说
不,不是的
所有的都是美好的
所有的,都
不,不是的
我低着头继续走路
朝我的灌水走去
捧着四颗,酸梅
迎接,水
汹涌的水或者
涓涓细流的,水
一丝一丝浸入的水
迎接,低着头迎接
就这么走,朝前走
然后就到了水的面前
水是没有表情的
或者是有的
应该看看
抬头,睁开眼睛
从睫毛缝隙间,偷窥
看见,水汹涌
或者涓涓细流
来到我的酸梅之间
进入塑料杯子的空间
热度使容器膨胀
热度使酸味弥散
我没有看,没有睁开眼
我盲目的灌水
热腾腾的蒸汽扑到脸上
寒毛,沾上了细小水珠的寒毛
微微颤抖,逐渐强烈的颤抖
灌水,灌水,灌水……
2001年夏
母亲
向北岛致敬
午夜,我穿过蒙霜的北京,
踏过地面,不留下脚印。
我愿逆流而上,寻你的爱情,
寻我不存在的出生证明。
在这午夜,我将穿过
大半个中国。飞跃过秦岭,
摘二十四年前的花,献你。
我采摘我一生的花束。
这里没有滚烫的物质,
我只葆有这午夜的青春。
我们共有的肾以及心脏,
是锁链两端的兽。
母亲,我捆绑自己,为你
做一个祭奠。你是一根鞭子。
在与此相同的时刻,我不能不
抽打自己,舔我们喷涌的血。
2003年春
下一篇:最后一页
X 关闭
财经排行
- 1、环球快讯:工信部:加快电力设备绿色低碳,发展高功率密度电机!
- 2、天天百事通!欧洲试图发展动力电池产业,却发现产业链掌控在中国手里
- 3、焦点信息:2022激光聚会活动回顾|ACS用于激光微加工的高性能运动控制系统
- 4、环球热推荐:丹佛斯服贸会携手三大国企,共创零碳未来
- 5、天天速递!精彩依旧,图尔克荣获2022CAIMRS两项大奖
- 6、环球速看:运用数字孪生+智能算法,行动元“末端振动抑制”技术超车欧美厂商
- 7、世界播报:锂电池快充或将突破技术难关
- 8、每日快讯!喜报!清能德创荣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称号
- 9、天天要闻:腾讯成国内首个获批创新医疗器械的互联网科技公司
- 10、环球消息!机器人的仿生之道
X 关闭
观点
-

【诗选】马雁令我心颤的诗
惊异,目视,爱,许多灵思和故事。选自《马雁诗集》,挑出个人尤其喜欢
-

带圈的11复制_带圈的11 天天聚看点
1、在Word中加入带圈11以上的数字序号方法:以2013版为例,光标定位在
-

微动态丨扫描机如何共享_如何共享扫描仪到另外一台电脑
1、扫描仪不用共享吧,只要共享扫描仪的默认文件就行了,并在接扫描仪
-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2023-06-03 01:40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前沿热点
音频解说一、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天气预报1、文山市气象台2
-

七天七夜重启天涯直播活动筹得20万
电商报快讯:6月4日消息,@重启天涯在微博公布此次七天七夜重启天涯活
-

麦收进度过三成 “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调度显示,全国麦收进度过三成,“三夏”大规模小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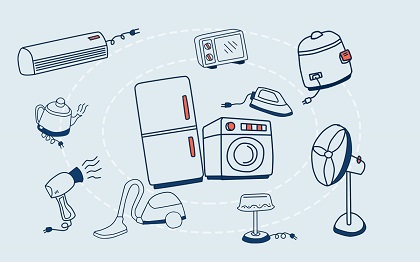
Scotto:篮网将长岛篮网主帅朗尼-布莱尔提拔为球队助理教练 天天热文
Scotto:篮网将长岛篮网主帅朗尼-布莱尔提拔为球队助理教练,沃恩,长岛,
-

进击的巨人墙壁的真相_进击的巨人墙壁
1、墙里有巨人。2、因为三面墙都是巨人做的,巨人皮肤变硬后,从巨人的
-

公克和克一样吗_公克和克有什么区别 一公克等于多少克
1、公克和克没有区别,在重量上是同等重量。2、一公克等于一克。3、公
-

资产的特征和确认条件分别是什么(资产的特征)
1、资产的定义中包含了资产的三个特征:(1)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2
